佛典音义,是汇集解释佛教经典中难读难解的字音和字义的著述。它产生的来源有二:首先是为读习佛典的需要。中国译经,始于东汉,历二百余年迄刘宋时,即已卷帙浩繁,义理丰富。其间古代学者对于各别经典多有注释,但对于一切经典文字的读音解义,需有音义专著详加注释,方能使学人从音通义,明白了解经论内容。而音义书的出现。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。其次是外受小学家的影响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列小学凡十家,均属于字书训诂之类。汉、魏以来的小学家,有许多有关字学、训诂、音韵之作,如孔安国、郑玄的《尚书音》,孙炎、郭璞的《尔雅音》,孙登的《道德经音》等。这不能不给佛家著述以相当的影响。刘宋时,慧叡开始以经中诸字与众音异旨为材料,著《十四音训叙》。到了隋唐之际,佛典音义书籍就逐渐多起来了。
佛典音义,与一般书籍的音义一样,有的仅注字音(如道慧《一切经音》,处观《绍兴重雕大藏音》三卷等),有的也兼释字义(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等)。从内容方面来分,大致有三类:一、音译部分的音义,二、义译部分的音义,三、咒语证音。
音译部分的音义,起源很早。东汉安世高、支娄迦谶、昙果、康孟详诸人翻译佛经时,对音译梵语即加以注释。其后,吴支谦、西晋竺法护、安法钦、法炬,东晋法显,齐昙景,姚秦鸠摩罗什等新译,也有音译注释。在这些音译注释基础之上,乃有《道行品诸经梵音解》、《翻梵言》、《翻梵语》等书的出现。这些是早期的佛典音义作品,没有音义之名,而且只限于音译部分。其次是义译部分的音义,这在音义书中占的份量较多,因为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,除了所谓“五不翻”必须用音译而外,其余大部分仍以义译为主。最后是咒语证音,这部分虽不太多,而它的应用价值却很大,可借以研究各时代汉语字音,解决音韵学上的许多问题。
另外从音义和经典的关系来看,它的内容又可分为三种:一、一经部分的音义,如窥基撰《法华经为为章》等,二、一经全部的音义,如慧苑撰《新译华严经音义》、净昇撰《法华经大成音义》等,三、一切经音义,如玄应撰《一切经音义》,慧琳撰《一切经音义》等。
佛典音义,从体制上看,又可分为三种:一、随函逐经注解的,如可洪撰《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》,云胜撰《大藏经随函索隐》(今佚)等。二、统一众经分韵编类的,如行均撰《龙龛手鉴》等,三、统一众经依文字部首编类的,如处观撰《绍兴重雕大藏音》等。
现存音义书中,以玄应与慧琳二家的著作最为重要。
玄应撰《一切经音义》二十五卷。本名《大唐众经音义》,道宣序及所撰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五,均用此名。其后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五著录此书,改名《一切经音义》。其实此书所注经籍,仅四百四十余种,未尽全藏。本书将藏经中难字录出,为之注音释义,广引群籍,大都凿然有据。但有不足之处,如庄炘谓玄应说字“以异文为正,俗书为古,泥后世之四声,昧汉人之通借,其识仅与孔颖达、颜师古同科”。这些缺点,在其后慧琳书中,始大部分得到纠正。
慧琳撰《一切经音义》一百卷。慧琳为不空三藏的弟子,于显密教及印度声明、中华音韵训诂之学都相当通达。唐德宗贞元四年(788),他年五十二,开始撰《一切经音义》,至唐宪宗元和五年(810),历二十三年撰成,书中所释,悉为《开元释教录》入藏之籍。始于《大般若经》,终于《护命法》,总一千三百部,五千七百余卷。有玄应旧音可用者用旧音,余则自撰。其释音多据《韵英》、《考声》、《切韵》等书,释义多据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玉韵》、《字统》、《古今正字》、《文字典说》,《开元文字音义》等书。其有诸书所不备者,则兼采儒经杂史百家之说。所引书籍,达二百四十余种之多。本书音义精核详审,前后诸家所作均不能出其右。除有助于读经注经之外,凡研究儒经诸史疑义,求之于注疏而不得者,也往往可于本书采获佐证。而且所引书传皆隋末唐初之本,文字审正,可以校正今本伪脱之失。但本书也间有以古字误为俗字的;有引《说文》窜改本的讹字而未能改正的,但不过是小疵而已。
佛典音义之较早出者有高齐释道慧所撰《一切经音》若干卷,见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八(转引自庄炘撰《唐一切经音义序》),但其书不传。此外尚有云公撰《涅槃经音义》一卷。慧苑撰《新译华严经音义》二卷。此外有窥基撰《法华经音训》一卷,太原处士郭迻撰《新定一切经类音》八卷(见日僧智证《请来录》,今佚),后周霅川西峦行瑫律师撰《大藏经音疏》五百卷(今佚)。后晋汉中沙门可洪撰《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》三十卷(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三称可洪进《大藏音义》四百八十卷,误)。辽希麟撰《续一切经音义》十卷(凡《开元录》以后至《贞元录》之间续翻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书二百二十六卷,本书都续注了音义)。其次有宋太祖乾德五年(967)释云胜(一作文胜)撰《大藏经随函索隐》六百六十卷(见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三,今佚)。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)释惟净等撰《新译经音义》七十卷(见《景祐录》卷十五,今佚)。南宋处观撰《绍兴大藏经音》三卷,清净昇撰《法华经大成音义》一卷等。
佛典音义在学术研究上还有几种作用,首先,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,所引群籍,关于儒经有郑康成《尚书注》、《论语注》、《三家诗》,贾逵、服虔《夏秋传注》,李巡、孙炎《尔雅注》。字书有《仓颉》、《三仓》,卫宏《古文》,葛洪《字苑》、《字林》、《声类》,服虔《通俗文》、《说文音隐》及《汉石经》之属,皆非世所经见。至于慧琳的《一切经音义》,希麟的《续一切经音义》,证引经、史等古籍更多,且大部分均已遗佚,皆可供学者补辑逸书之用。其次,许氏《说文解字》,乃文字体制兼训诂之书,在小学中非常重要。二千年来,展转传抄,其中伪脱、讹音、错字、逸句等不一而足,琳、麟二家音义所引,大都可以补正,足供语文学者研究参考。又密咒一部分,因夙重音读,它的翻译与注音均经严格的选择,而保存字音比较正确;另一方面梵文的音读,虽经过长久时间而变化甚少,故以梵文原音为标准,刊定咒语的音译,对考定译音时代汉字的音读提供了便利。凡此均可供音韵学家研究汉语古音参考之用。
一切经音义
《一切经音义》一百卷,唐释慧琳撰。慧琳(737~820),唐京师西明寺僧,俗姓裴氏,疏勒国人,幼习儒学,出家后,师事不空三藏,对于印度声明、中国训诂等,都有深入的研究。他认为佛教音义一类的书籍,在以前虽有高齐释道慧撰《一切经音》(若干卷),唐释玄应撰《众经音义》(二十五卷),云公撰《涅槃经音义》(一卷),慧苑撰《新释华严经音义》(二卷),窥基撰《法华经音训》(一卷)等等,但有的只限于一经,有的且有讹误。因在各家音义基础之上,他更根据《韵英》、《考声》、《切韵》等以释音,根据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字统》、《古今正字》、《文字典说》、《开元文字音义》等以释义,并兼采一般经史百家学说,以佛意为标准详加考定,撰成《一切经音义》百卷。自唐德宗贞元四年(788)年五十二开始,至唐宪宗元和五年(810)止,中经二十三年方才完成。后十年,即元和十五年年八十四,卒于西明寺。
本书为经典文字音义的注释之作。它将佛典中读者与解义较难的字一一录出,详加音训。并对新旧音译的名词,一一考正梵音。所释以《开元释教录》入藏之籍为主,兼采西明寺所藏经,始于《大般若经》,终于《护命法》,总一千三百部,五千七百余卷(此据景审《一切经音义序》说,实际不足此数),约六十万言,凡玄应、慧苑、云公、基师等旧音可用者则用之,余则自撰。其用旧音之处,也往往加以删补改订(其用云公及基师音义,皆注明删补,又引用《玄应音义》也多所改订,如第九卷《放光般若经》卷一“绪,旧作辞吕反,今改用徐吕反”。“甫,旧作方宇反,今改用肤武反”。“俞,旧无反切,今补庾朱反”等等)。本书撰成后,于宣宗大中五年(851)奏请入藏。后经变乱,本书之存于京师者亡佚。后五代时契丹据燕云十六州时,本书在契丹流行。后周世宗显德二年(955),高丽国派人来吴越求本书不得。至辽圣宗统和五年(987),燕京沙门希麟继玄应书,撰《续一切经音义》十卷(就《开元录》以后至《贞元录》间,续翻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书,约二百二十六卷,为之注音解义)。后来辽道宗咸雍八年(1072),高丽国于辽得本书。元至元二十三年释庆吉祥撰《法宝勘同总录》,著录此书,可见元时此书犹存,其后一度亡失。到光绪初年,我国复从日本得到此书,民国元年(1912)始由上海频伽精舍印行。
本书内容精审,非前后诸家音义所能及。它在学术上的影响,有下列几方面:首先,是对佛教义学的贡献。佛典繙自梵文,无论是意译或直译,均难免有所讹略。且笔受者往往“妄益偏旁,率情用字”,而书写者又随便增减点画,不但“真俗并失”,而且“句味兼差”。加以长期间展转传钞,错误更多(如“羯鞞”写作“鹖鷎”,“鞭[革+亢]”写作“[革+亢]”,“厞礨”写作“蓓蕾”、“莇”写作“薅耡”,“庶几”写作“謶譏”,“狎习”写作“謵”,“被褡”写作“被闟”等等)。使人多有隔膜。慧琳注释佛经,一本汉儒小学家以字音释字义的原则,使人由普通义而明其理。这样,开元入藏的佛经,由于此书之助,大都可以理解。
其次,是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。东汉许慎撰《说文解字》一书,成为训诂学的标准,惟传本不一,经后人刊落,伪误甚多。如用慧琳《音义》对勘,就知后人所刊《说文》中有逸字(如《说文》无“濤”字,而琳《音义》八十三卷,引《说文》云;“濤,潮水涌起也,从水寿声”)、脱字(如《说文解字后叙》谓说解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,胡秉虔氏撰《说文管见》谓说解止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。据此则说解脱漏一万零七百四十二字,而琳《音义》卷二与卷六《大般若经》癎字注引《说文》云:“风病也。”今说文即脱“风”字)、逸句(如本书卷十三与十四《大宝积经》及《集古今佛道论衡音义》,“桎梏”注引《说文》云:“桎足械也,所以质地也,梏手械也,所以告天也。”今《说文》逸“所以质地也,所以告天也”二句)、删改句(如本书卷九十八《广弘明集音义》,“瑶”注引《说文》云:“石之美者也”。徐《说文》改石为玉)、传写讹误的字句(本书卷八十六与九十六《辩正论》及《广弘明集音义》,甃注引《说文》云:“井甓也”。徐《说文》误作璧),凡此均可以用慧琳《音义》增补订正。可见此书在文字学上的价值。
复次,是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。《说文解字》一书,素为研究古音者的准则。惟《说文》古音经南唐二徐刊定之后,被窜乱者不少,而慧琳《音义》所引《说文》,则能保存古音,可为研究古韵和音读者之助。唐,宋韵书,多祖陆法言《切韵》一派,《切韵》为六朝旧音,保存于江左,因此唐人称为吴音。另外还有元廷坚《韵英》及张戬《考声切韵》一派为秦音。慧琳熟悉关中汉语,所以本书独取元廷坚《韵英》一派的秦音(王国维据景审序,谓琳音音切依据元廷坚与张戬书,而本书注中却指明专依廷坚的《韵英》),而不取陆法言一派的吴音,(如本书卷八檛打下注云:“下德耿反,陆法言云:都挺反,吴音,今不取”。如本书卷首音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复载二字云:“上敷务反,见《韵英》秦音也;诸字书皆敷救反,吴、楚之音也”。)可见一斑。后世,《切韵》一派的吴音盛行,而《韵英》一派的秦音衰歇,今可藉书上窥往古的关中音系。又本书卷五音玄奘译《大般若经》第四百十五卷,四十三梵字,悉改旧文,谓奘译为边方不正之音,因此摈而不用。这是因为玄奘所学梵文为当时中天竺音系,慧琳所学则为北天竺音系(但慧琳自称为中天音),故有参差,特加改易(慧琳书对旧翻陀罗尼有梵本可考者,都重新译过。如《大般若经》护法陀罗尼,《十轮经》护国不退转心大陀罗尼,《涅槃经》波旬献佛陀罗尼等。又于《涅槃经》音义附辨悉谈十八章)这也是对于梵文音韵研究方面可资之处。
本书在国内久已失传,自清光绪初年复得之于日本,即为学术界所重视。一般学人对它的利用:一为辑佚,二为考史。因为本书所用材料,都是隋唐时代通行的古籍,而且征引广博,计经、史、小学书籍共达二百四十余种。其中所收经部如郑玄《周易注》、韩康伯《周易注》等,史部如宋忠《世本》、姚恭《年历帝纪》等,小学部如李斯《苍颉篇》、赵高《爰历篇》、《文字典说》、《古今正字》等久已亡佚。所以自本书取回后,会稽陶方琦即利用它辑《苍颉篇》以补孙星衍之不足。又续辑《字林》以补任大椿之不足。山阳顾震福利用它辑《苍颉》、《三苍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文字集略》四十六种,为《小学钩沈续篇》(任大椿辑小学逸书二十四种名曰《小学钩沈》)。此外如汪黎庆辑《字样》、《开元文字音义》、《韵诠》、《韵英》四种为《小学丛残》,易硕辑《淮南许注钩沈》,十之八均取材于《慧琳音义》,十之一取材于希麟《续音义》,采用他书者不过十之一而已。本书还可用以考史。如敦煌发见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,首尾残阙,不知何人所作。罗振玉据本书卷一百所标难字,考知为慧超所撰。近人陈援庵考《四库提要》惠敏《高僧传》之伪,利用本书卷八十六考知为慧皎书之前帙,等等皆是。另外本书还保存了一些佚书目录,如《五天雅言》、《七曜天文经》、《西域志》、《南海志》、《崇正录》、《释门系录》、《利涉论衡》、《道氤论衡》、《无行书》,稠禅师《宗法义论》等。
本书也有一些粗疏之处。即间有以古字误为俗字的,有引《说文》窜改本的讹字而未能正其误的,也有因失检而自错乱的(如浮字凡五见,卷七浮囊下注浮附五反,玉篇音扶尤反,陆法言音薄谋反,下二反皆吴楚之音,今并不取。然卷三浮囊下注浮,又用符尤反)。但这些只不过是小疵而已。
(田光烈)







 净界法师
净界法师 道证法师
道证法师 弘一大师
弘一大师 虚云老和尚
虚云老和尚 莲池大师
莲池大师 妙莲老和尚
妙莲老和尚 太虚大师
太虚大师 慧律法师
慧律法师 圣严法师
圣严法师 净慧法师
净慧法师 大安法师
大安法师 印光大师
印光大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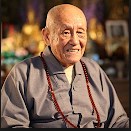 梦参老和尚
梦参老和尚 其他法师
其他法师 宏海法师
宏海法师 界诠法师
界诠法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