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,简称《至元录》,十卷,元代释庆吉祥等撰。
至元年间,元世祖“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,疑其有异,命两土名德对辩,一一无差。帝曰:‘积年疑滞,今日决开’。”(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二十二引《弘教集》)由此有法宝勘同之举。此事系至元二十二年(1285)开始,即本书叙录所说:“大元世主……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,召西蕃板底答、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、湛阳宜思、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,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、及畏兀儿斋牙答思,翰林院承旨旦压孙、安藏等,集于大都大兴教寺,各秉方言,精加辩质。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,顶踵三龄,诠讐乃毕。”于是“复诏讲师科题总目,号列群函,标次藏乘,互明时代,文咏五录(即指引用的唐代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》、宋代的《大中祥符法宝录》、《景祐新修法宝录》、元代的《弘法入藏录》),译综多家”,而成本书。本书的主要内容因系对勘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的异同,所以题名作“勘同总录”。
本书卷首列有庆吉祥为首的编修、执笔、校勘、校证、译语、证义、证明诸人的衔名,共二十九人。庆吉祥等十五人系汉僧(名字下带有吉祥字样,当是受其时藏僧常以吉祥命名的影响)。其中演吉祥本名定演,事迹见赵孟頫所撰的《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》(《松雪斋文集》卷九)。又元廷官吏五人中,迦鲁拿答思和安藏在《新元史》卷一百九十二中有传。
本书分两部分,第一部分总叙,标示本书的缘起和大纲,又分四科:第一是“总标年代,括人法之弘纲”,简单地记录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到元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二个朝代译出三藏的部数和卷数。第二是“别约岁时,分记录之殊异”,列载后汉到元五个阶段中译人和传译经典的数字。第三是“略明乘藏,显古录之梯航”,著录《开元》、《贞元》、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、《弘法》等录所记的经律论部卷数目。第四是“广列名题,彰今目之伦序”,标明本书的分类和部卷数目。第二部分是本书的正文,文前有一段说明:从有翻译以来经律论等的卷目、年代、译人事迹等在《开元》等录中,已有记载,对于这一方面即不再详述,而只按类分载各经。
本书的分类是按契经(经)、调伏(律)、对法(论)三藏,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,末尾有圣贤传记录。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二类。显教大乘经中又分《般若》、《宝积》、《大集》、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诸大乘经六部;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部。在菩萨对法藏中分大乘释经论和大乘集义论二类。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(指汉地)圣贤集传二类。这种分类法,大致是依据《开元释教录》。如关于菩萨契经藏以《般若》部居首,小乘契经藏以《阿含》居首,及圣贤传记所包括的内容等的说明都是照《开元录》原文迻录。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,则是本书所独具。自唐宋以还,密部教典翻译日多,附列在显教经籍中已不易包容,同时,藏传佛教在元代极为朝廷所重视,把密教和显教并列,正反映出密教在当时佛教中的地位。也有可能,显密并列是受藏文藏经目类归类的影响。例如现存的古录登迦目录,在大乘经、小乘经而外,另列“秘密呾特罗”一大类。后来的藏文经录,一般也是分为经部和续部,因而为《至元录》所采用。兹将本书的分类和经典部、卷数目(依实际数目)表列如下:
┌般若部─── 40部 794卷┐
│宝积部─── 84部 177卷│
┌显 教┤大集部─── 27部 156卷├ 535部┐
│大乘经│华严部─── 31部 239卷│2304卷│
┌菩萨契│ │涅槃部─── 6部 59卷│ │ 885部┐
│经 藏┤ └诸大乘经──347部 879卷┘ ├2945卷│
契经藏┤ │密 教┌秘密陀罗尼─261部 527卷┐ 350部│ ├1176部 3656卷
│ └大乘经┤ ├ 641卷┘ │
│ └仪轨──── 89部 114卷┘ │
└声闻契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281部 711卷┘
┌菩萨调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28部 56卷┐
调伏藏┤ ├ 98部 564卷
└声闻调伏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70部 508卷┘
┌大乘释经论─ 21部 157卷┐
┌菩萨对法藏┤ ├117部 631卷┐
对法藏┤ └大乘集义论─ 96部 474卷┘ ├155部 1339卷
└声闻对法藏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38部 708卷┘
┌梵本翻译集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95部 231卷┐
圣贤传记┤ ├214部 1607卷
└东土圣贤集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119部 1376卷┘
本书的组成是以《开元录》所载为骨干,再以《贞元》、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、《弘法》等录所载补充,故引用《开元录》经目所占比重量大,约近四分之一。
本书是以藏文大藏经目录,对勘汉文经藏(见卷首释净伏序),凡是有汉译本同时也有藏译本的,很多将梵文原名用汉文音译注在经名之下,作者在《般若》部的梵名下发凡起例说:“今此总录,于题目内间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,自来三藏但以梵文译为华言,所以不存梵名。间有存者,于五义中亦有具一二义故不翻者也。今因与蕃相对,随彼蕃云有无记录,有者著之,无者仍旧。或有的对,或约蕃义,不可一准也。义学高德善二音者,请勿疑矣。”(卷一)这是因为藏文翻译的经典,卷首大都保留着梵文原名的音译之故。汉文与藏文译本有不同之处,则勘其同异,加以注明。如《大般若经》第一会下加注:“此会经与蕃本《十万颂般若》对同。”小注,“此会比西蕃本多‘常啼’、‘嘱累’、‘法涌’三品,其蕃本却在第五会中”。又在同经第五下加注:“此会经与蕃本《八千颂般若》对同。”小注“此会比蕃本少‘常啼’、‘法涌’、‘嘱累’、‘慈氏所问’四品,前三品却在前第一会中‘慈氏所问品’全阙”(均见卷一)。又如《大集会正法经》下注:“此经与蕃本相对,彼经稍少”(见卷二)。《华手经》下注:“亦名《摄诸善根经》,此名与西蕃本同”(卷三)。这些校勘,对于研究汉藏教典是很好的资料。在校勘过程中,也提出一些问题,如《大方等大集经》下注说,“梵文云,此《大集经》一十一分,四十八品,品局当部,分及支派。今勘本经总有八品三分,于三分中曲分二十八品,共成三十六品。云四十八,未详所以”(卷二)。这还有待于后人的研究。至于某些藏文译本有疑问的经,如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(见卷一)、《观虚空藏菩萨经》(见卷二)、《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》(卷六),都注明“蕃疑,析辨入藏”等字样。
本书着重在汉藏对勘,著录的典籍方面,唐以前同于《开元》、《贞元》二录,宋代同于《祥符》、《景祐》二录,所增补的不多。著录辽代、元代的译述,仅只慈贤、思孝、非浊、八思拔、安藏等数人。但是本书所征引的《祥符录》、《景祐录》,现只存残本,《弘法入藏录》久已失传,从本书中还可以了解三录的内容。 本书在对勘汉文藏文方面,虽大力进行,但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。第一,同本异译的经,因为立名不同,有的则注“蕃本有”,有的则注“蕃本阙”,而表现出自相矛盾。如《大宝积经》第十二《菩萨藏会》,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一),《佛说大乘菩萨藏正法经》,虽注明与上经同本,但却说“蕃本阙”(卷四);又如《大乘日子王所问经》,注明与《优填王经》同本(卷四),《优填王经》即《大宝积经》第二十九《优陀延王会》,注云 “此会与蕃本同”(卷一),而《大乘日子王所问经》却注“蕃本阙”(卷四)。第二,有些同本异译的经,没有勘出,因而在加注藏文本有无上也不一致。有如《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》与《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》,注云“同本异译,蕃本阙”(卷三),而《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》则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四),不知此三经原系同本异译。又如《善法方便陀罗尼经》与《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》、《护命法门神咒经》,注云“同本异译,蕃本阙”(卷五),又如《延寿妙门陀罗尼经》则注云“与蕃本同”(卷六),不知此四经原系同本异译。第三,有的经不是同本,误作同本,如《妙法圣念处经》下注“与《大宝积经》第四十三《普明菩萨会》同本”(卷四),实际是错误的。第四,在对勘藏文本时,常常依据书名判别有无,而实际不然。如《阿毗达摩集论》、《杂集论》,皆注“蕃本缺”(卷八),而实际皆有藏文本。又如《观所缘论护法释》,注“蕃本同”(卷九),而实际缺藏文本。这类例子很多。第五,在梵名经题上,也间有错误。如《大宝积经》第二十九《优陀延王会》,梵题作“阿唎亚 乌答亚拿 哇忒萨 阿啰扎 拿麻 八哩 哇哩怛 八哩巴哩赤”(卷一),后半应作“八哩巴哩赤拿麻巴哩哇哩怛”。《优填王经》与上经同本,梵题作“阿唎亚 乌达牙拿 哇忒萨 阿啰扎 拿麻八哩瓦八哩巴哩赤 啰答”(卷一),后半也应作“八哩巴哩赤拿麻八哩瓦啰答”。又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梵题作“晡怛 阿瓦怛萨甘 拿麻麻诃布噜亚 摩诃衍那 苏怛啰”(卷二),摩诃下脱vai字之音译。另外有的梵题和汉译经名配合错误:如《大宝积经》第十五《文殊师利授记会》,注云“蕃本阙”,然第四十六会《文殊说般若会》的梵题“阿唎亚 曼殊师利 哺怛 乞室怛啰 孤拿 尾喻诃 拿麻 摩诃衍那 苏怛唎”(卷一),正是第十五会的梵名,而不是第四十六会的梵题。又如《般舟三昧经》与《拔陂菩萨经》、《大方等大集贤护经》是同本异译,注说“蕃云对同,未见其本”(卷二),所以没有梵名,但是《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》的梵题“阿唎亚 钵拿 帝乌都巴拿哺怛三穆迦 阿瓦思滴怛 三麻帝拿麻 麻诃衍拿 苏怛啰”(卷五),就是《般舟三昧经》的梵名,与《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》则毫无关系,都是对勘误解所致。最后第六,在译人方面,也间有错误,如《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》作施护译,《圣观自在菩萨梵赞》作法贤译(卷十),但在《祥符录》卷七上都作法天译。此外,误题、漏注或重复之处尚多。
汉藏佛典的对勘,本是艰巨的事业,在当时政府的主持下,集合了许多汉藏有名的专家来工作,经过三年的时间,完成了这部巨著,对于佛教经典目录的整理研究,有其一定的作用。本书保存下来的经论梵名译音,可供语言音韵学家作参考,所勘藏文经典的有无,也是研究古代藏族佛教有价值的资料。后世在经典分类上,以密教独立为部,如明寂晓的《释教汇目义门》,智旭的《阅藏知津》,都是受本书的影响。
本书在清代乾隆年间(1736~1795),工布查布著藏文本《汉土佛教史》曾抄译本录为其最后一部分。又1883年日本南条文雄英译《大明三藏圣教目录》,也曾利用本录,注出各书的梵文原名。由此可见本录应用之广。
(苏晋仁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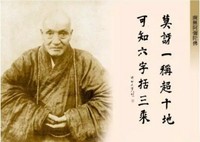



 净界法师
净界法师 道证法师
道证法师 弘一大师
弘一大师 虚云老和尚
虚云老和尚 莲池大师
莲池大师 妙莲老和尚
妙莲老和尚 太虚大师
太虚大师 慧律法师
慧律法师 圣严法师
圣严法师 净慧法师
净慧法师 大安法师
大安法师 印光大师
印光大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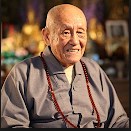 梦参老和尚
梦参老和尚 其他法师
其他法师 宏海法师
宏海法师 界诠法师
界诠法师